“文化大革命”发生于1966年至1976年,史称“十年浩劫”。“文革”时期,各项事业遭受到严重破坏,教育事业也在劫难逃。
1967年2月,益都县成立了文教局革命造反委员会。6月,改称益都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文教办公室。1968年,全县的教育工作由益都革委政治部宣传科管理。下面的公社革命委员会也相应成立教育革命领导小组,配备了文教干部,并成立了教研组,设组长、会计、教研员,负责全公社联中、小学的教学工作。1976年3月,益都县改设革命委员会文教局,负责全县教育工作。
“文革”期间的教师队伍极不稳定。1968年底,因“侯王建议”,1400名公办小学教师调回
青州原籍,致使平原的教师过剩,只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,而杨集等山区公社竟无一名公办教师,教育一度瘫痪。1969年,联办初中和社办高中大量出现,不少低于中师或高中文化程度的小学教师改教初中,原初中教师改教高中,师资水平明显下降。此时民办教师剧增,据1976年统计,全县小学教师4329人,中学教师2791人,师范教师44人,其中民办教师3879人,占一半以上。
“文革”期间,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遭到践踏,教师被污蔑为“臭老九”、“教唆犯”、“反动学术权威”、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。许多人被批判、揪斗、游街示众,县教育局干部周维、教师李金生、许德政、郭建初等17名教师被迫害致死。教师被弄得无所适从,欲干不能,欲罢不忍,处境十分困难。直到1976年10月粉碎“四人帮”,批判了“两个基本估计”,党中央明确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、是依靠的力量,教师才得到社会的尊重。
“文革”期间,“踢开党委闹革命”,党组织瘫痪,群众组织说了算。教师下放到生产队后,党员关系转到生产大队,组织生活极不正常。“文革”初期,共青团组织曾带领青少年破“四旧”。“红卫兵”组织成立后,团委、团支部名存实亡。1967年,林彪、江青一伙以“少先队基本上是少年儿童全民性组织,它抹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,根本不突出毛泽东思想,实际上失去了先锋战斗作用”为由,取消了少先队组织,改建为“红小兵”。组织“红小兵”参加“造反”、“批判资产阶级”的运动。这时的学生会被解散,由“红卫兵”组织代替。“文革”期间,思想政治教育被引入“极左”的歧途,政治课只是学毛主席语录、学报刊社论和斗私批修。“四人帮”抛出“两个基本估计”后,“极左”思潮进一步泛滥,师生思想极度混乱。
“文革”期间,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也不正常。1966年7月14日,毛主席以73岁高龄畅游长江,国家将每年7月16日定为“游泳节”。中小学生积极响应“到江河湖海去锻炼”的号召,利用自然水域开展游泳活动。1967年3月7日,毛主席对天津延安中学的材料做了“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”的批示后,益都驻军6197部队对全县中小学实行军事训练,传授列队、刺杀、射击、投弹等军事知识,而这时的学校卫生工作竟无人过问。
“文革”开始时,幼儿教育处于瘫痪状态,农村幼儿园全部停办。城里的幼儿园只是领读毛主席语录,教唱语录歌曲,学唱革命样板戏选段。
“文革”期间,工农小学停办,全日制小学“停课闹革命”,“红小兵”全部参加“造反”,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。1968年,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办,教学设备不足,学校秩序混乱,不少学校因无师资而关门。“工宣队”、“贫管会”进驻学校,要求“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”,学生“以学为主,兼学别样”,“学工、学农、学军,也要批判资产阶级”。形式上复课,实质上只是胡闹腾,教学根本没有纳入正规。1972年,继续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,提倡民办小学。因片面强调数量,导致学校盲目发展,全县小学猛增到948处,学生达98583人。1974年在校生121770人,比1972年增加23000人。因校舍、教师、教学设备都跟不上,出现了“黑屋子、危房子、土台子、泥孩子”的状况。为解决师资缺乏问题,只得从中小学毕业生中选用教师,而新选用的教师不少是“造反”起家的红卫兵,根本不会教学,教育质量严重下降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初始,全县中学相继停课,并停止招生,毕业生“留校闹革命”。直到1968年才“复课闹革命”,但仍旧动荡不安。农中全部瘫痪。1969年,中学管理下放到公社,在“上高中不出公社,上初中不出片”的口号下,中学飞速发展。一中改为益都县中学,由县管理,其他初中改为社办高中。原来没有中学的公社也办起了高中,校名随公社名称叫“某某中学”。于是,高中由原来的1处发展为21处,在校生2941人。初中改为大队联办,称作联中。全县联中336处,学生达24785人。由于师资、设备、经费等条件的限制,教学质量很低。1970年后,小学附设初中班,联中增设高中点,全县除21处高中外,又设高中点56处,高中生达16629人,初中生46927人,教职工3370人。
青州的“文化大革命”,首先是从益都师范开始的。1966年6月,益都师范贴出了昌潍地区“第一张大字报”,点燃了整个潍坊市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烈火。师范的教师和学生分为两大派,“停课闹革命”,武斗十分激烈。师范教导主任李金生、语文教师许德政、生物教师汤伯显等三位教师被活活折磨致死。校舍及其教学器材遭到严重破坏。师范连续两年没有招生,1966年毕业生延至到1968年才毕业。同年,采用群众推荐的形式,招生265人,两年后离校,再未招生。学校在没有学生的情况下,只举办学习班、培训班、进修班。直到1975年,才招160名公社推荐的“社来社去”中师班,毕业后回乡任教,先为民办教师,后来转为公办教师。10年中,师范基本没有学生,造成了中小学教师队伍的青黄不接,给教育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。
“文革”期间,中学教育遭受到的破坏相当惨烈。上级要求“课程设置要精简”,中学只设政治、语文、数学、工农业基础知识、军体、劳动课。一味突出政治,“念念不忘阶级斗争”,学“语录”,学社论,政治口号充斥课堂内外。采取走出去、请进来的方式,以干代学,严重违反了教学规律。
以青州一中为例,可以看出“文化大革命”对教育的破坏程度。“文革”前,青州市只有这一处高中。一中领导班子长期稳定,领导成员精通业务,善于管理,带出了一支水平高超、治学严谨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师队伍,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,树立了“刻苦勤奋、踏实严谨、紧张活泼、朴素诚恳”的优良校风,教学质量一直很好。1959年高考平均分列全省第二名,1962年,《光明日报》报道其办学经验,在全国推广。一中建校17年,共毕业35个班,1490名学生,升入高等院校1040人,占毕业生总数的70%。而“文革”中,全县1年高中在校生是“文革”前17年高中生总数的11倍,“文革”10年被荐入大专院校的仅339人,教育质量悬殊可想而知。
益都师范引燃了地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烈火后,青州一中被污蔑为“修正主义黑样板”,被指责为“十七年黑线专政”,是“封资修的大染缸”。红卫兵组织一夜兴起,学校被迫停课,领导班子瘫痪,阎石庵校长被打成“走资派”,王子政主任及一部分优秀教师被打成“反动学术权威”、“牛鬼蛇神”,动辄贴大字报、剃光头批斗、挂牌子游街,惨无人道地折磨教师,团委书记郭建初被关押致死,另两名职工因不堪遭受批判而投水而死。各派红卫兵组织互相斥责对方为“保守派”,自我标榜为“左派”,派性斗争日益加剧,武斗不断。学校财产、教学设备遭到严重破坏。1967年,学校成立“三结合”的革委会,派性斗争陷入了全面“内战”的局面,学校更加混乱。1968年,“清理阶级队伍”,校长及部分教师遭到更加残酷的摧残。图书管理员李治滨,因“逼供信”受尽折磨而投井自尽。8月,“军宣队”、“工宣队”先后进驻学校,领导“斗、批、改”,组建革委会,进行“教育革命”。11月13日晚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“侯王建议”,“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”。学制改为小学5年,初中2年,高中2年。一中教师分到各公社去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,学生也回本公社上学,一中基本上解体。1969年,开展“一打三反”、“清查5·16”运动,广大教职工再次遭受迫害。1970年,益都县革委将一中改为“五七红校”,灌输两条路线斗争史。1975年,“四人帮”掀起“批邓、反击右倾反案风”的运动,教育界掀起批判“奇谈怪论”的浊浪,报刊也发表《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》的文章,工作组又重新进驻学校,推广“大寨教育革命经验”,把师生拉到山区大寨田劳动,实行“开门办学”、“同十七年对着干”。然而,所谓的“教育革命”违背了教育规律,“对着干”已很不得人心。
1976年10月,一举粉碎了“四人帮”,十年动乱终于结束。在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,拨乱反正,改革开放,教育事业进入了空前未有的光辉时代。 (刘继孔)

“文革”期间教师支援农业

“文革”期间校办工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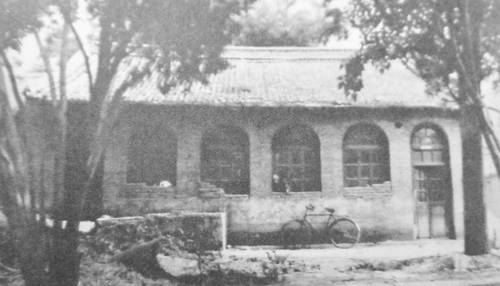
“文革”期间遭到洗劫的松林书院

“文革”期间中学毕业生回乡务农
编辑:今日青州网

